

央視新聞客戶端點擊或掃描下載
 國內國際圖片生活軍事人物科技文娛經濟評論
國內國際圖片生活軍事人物科技文娛經濟評論

原標題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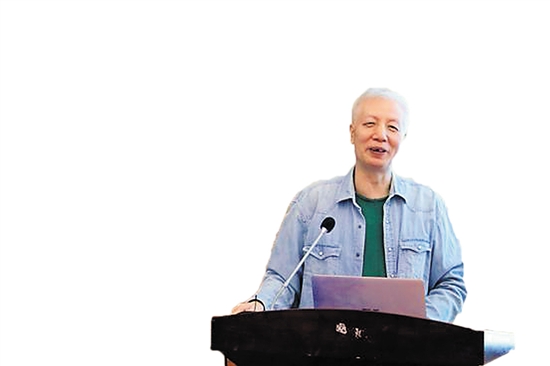

鮑十2003年出版的小說集《拜莊》,內收錄《子洲的故事》
□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杰
近日,導演李智與作家鮑十簽署合同,就改編鮑十小說《子洲的故事》達成共識,雙方將聯手打造一部同名電影。《子洲的故事》是一個具有巨大市場價值的文學IP(可用于改編電視劇、電影等的版權素材),2006年8月獲得第七屆“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·文學獎”。
李智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時表示,鮑十的《子洲的故事》讓他讀到了一個時代和一代人的特征。小說講述的是一個普通小男孩的故事:學識豐富卻窮困潦倒的父親,漂亮能干但拜金疏冷的母親,十二三歲的少年說不出誰對誰錯。父親病逝之后,他獨自從城市去到小鎮,投奔孤身一人的爺爺,并決定不再回去……李智認為,《子洲的故事》是一部中國版的《綠皮書》,講述中國農村與城市價值觀的碰撞。“通過孩子的視角看待大人的世界是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。”他告訴記者,小說中爺爺、兒子和孫子三代人的真摯情感,讓他兩度落淚。
李智在七八年前經朋友介紹看到《子洲的故事》,當時對故事就已經很感興趣。他認為,中國電影需要以內容說話。“今天,中國的觀影人群已經走向理性化,創作人員需要用好的故事做到藝術和市場的雙豐收。”雖然鮑十的故事非常細膩,但在電影表達上還有需要調整的地方。李智表示,目前他和他的團隊正在對《子洲的故事》進行改編,希望能從原故事出發,帶出對社會價值觀的思考。
《子洲的故事》是電影《我的父親母親》的姊妹篇。鮑十的中篇小說《紀念》被改編成電影《我的父親母親》,影片獲得第五十屆德國柏林電影節銀熊獎、1999年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影片獎、第23屆百花獎最佳影片獎、第20屆金雞獎最佳影片獎、上海影評人獎優秀故事片獎、美國圣丹斯電影節大獎、伊朗國際電影節紫水晶獎等。
據悉,電影《子洲的故事》將于今年年底開機,2020年上映。鮑十就此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專訪。他表示,《子洲的故事》這部小說是寫給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,反映一個時代的歷史烙印。
訪談A想寫文化人的境遇
羊城晚報:這次《子洲的故事》改編成電影的契機是怎樣的?
鮑十:《子洲的故事》發表已經有20年了,說實話這件事讓我有點意外。今年三月份的時候,導演李智通過朋友找到我,詢問購買小說版權事宜。很快他就來廣州簽了合同。最初商量的時候,導演還提出讓我做編劇。出于身體和時間各個方面的考慮,我婉拒了,建議他另請人來做編劇。還有一個因素,就是我也不想重復投入到這個故事當中。同樣的事情讓我做第二次,我也提不起什么興趣了。
羊城晚報:《子洲的故事》在您的創作中是一部怎樣的作品?
鮑十:這部作品創作于上個世紀90年代,與《我的父親母親》的原作《紀念》是前后腳發表的。我希望通過《子洲的故事》,寫一下當時文化人的那種境遇,包括他們的生存狀況、精神狀態,等等。《子洲的故事》只是個殼,內核是想表現和探討文化人在社會上的那種尷尬,他們既沒錢又沒權,然而又特別“執迷不悟”。小說發表之后,收錄到了我的一個集子里。有些朋友看到后,都說寫得不錯,甚至有人為之落淚。李智導演告訴我,他看這篇小說的時候也很感動。我估計就是這個故事中的那份情感打動了他。
在這個故事里,子洲的父親在群藝館工作,業余寫小說。生活窮酸,為人固執,身邊沒有人待見他。他的同學、朋友,包括他的老婆都不拿他當回事。而在他的老家,一個小鎮上,人們對他的態度卻截然相反。鎮子上的很多人,包括他的初戀情人,覺得他能寫小說,能在報紙刊物上發表文章,是很有出息的事。我就是要通過這樣的一種對比,來表現這樣一個現象。我也不知道這個現象能說明什么。
能談得來,有感覺,是我跟導演合作的前提
B
羊城晚報:您怎么看待在電影改編中小說作者的角色?
鮑十:電影是導演的藝術,它是以導演為中心的。作為原作者也好,編劇也好,在創作的時候可能都需要服從導演的感覺。這是它的一個特點。那么作者就要理解這一點。但這并不是說其中沒有作者本人的聲音。如果你跟一個好的導演合作,導演和編劇之間互相尊重、互相啟發,編劇就能把更好的東西提供給導演。導演有眼光,也會認可這些東西,使得作品增色。如果遇到了一個糟糕的導演,編劇的好想法他不予采納,其實作者也是沒有辦法的。
羊城晚報:您是如何選擇導演的?如何和導演合作?
鮑十:根據我有限的經驗來看,主要是看跟導演能不能談得來。能談得來,有感覺,這個是合作的前提。實際上我并沒有主動寫過電影劇本。從《我的父親母親》開始,都是別人找的我。一直以來,我都是按照我的節奏,從我的本心出發,慢悠悠地在寫小說,也沒想過要改編成影視。在《我的父親母親》之后,也有一些導演來找我,有的報酬還挺高,但我基本都拒絕了,原因就是談不攏,沒感覺。后來我只跟導演張加貝合作了兩部電影。一部是《櫻桃》,公映了,也獲得了幾個獎。張加貝是日本華僑,在日本做電影,曾經拍過一部《陶器人形》,有一定影響。那年他從日本給我打電話,想拍一個關于母愛的故事,因為看過《我的父親母親》,覺得我能寫好這個故事,于是就找上我。我并沒有馬上答應。我建議他,我們最好見個面聊一聊,有感覺了再決定合不合作。后來他從日本回來,我們在上海見面,談了幾天,有點感覺,我就給他寫了《櫻桃》。第二次合作的電影叫《天上的風》,沒有公映。
羊城晚報:小說家在作品中很犀利地寫出人性的復雜,但在電影中未必能夠完全呈現。您怎么看待這種取舍?
鮑十:一般情況下,小說要比電影豐富。小說是以文字來表現的,所以想象的空間、輾轉騰挪的余地都非常大,能夠充分表達作者自己的感受,比方描寫一個女人的美,你可以無限想象她的美。電影在這個方面就是弱項了,因為它把你想象的東西固定下來了。不過它的表現很直接、很直觀。所以說,小說中的一些內容,電影是沒辦法完全呈現的,只能說是一種遺憾的藝術。但一部好的電影,它會盡可能最大限度地把文字所要表達的表現出來。經典的電影一般都能做到。
另一個方面,電影中要表現的東西,文字也未必能夠做到。比如一個非常經典的表情,可能多少文字也說不出來。所以我的理解是,文學與電影各有所長。現在有一些寫小說的人,輕視電影創作。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。一部電影制作出籠,是用真金白銀砸出來的。把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,也需要嚴格篩選。他(導演)或者要考慮票房的因素,或者要考慮有沒有獲獎的可能。當然,電影的制作水平良莠不齊,但作家隊伍里也有垃圾作家。所以你沒有必要也沒有資格輕視別的藝術門類。換一個角度來說,作家的作品發表了、出版了,再改編成電影電視劇,客觀上起到推廣文學作品的作用,何樂而不為?所以沒有必要拒絕它。
不建議年輕寫作者一出來就寫電影、電視劇本
C
羊城晚報:在中國電影創作發展的過程中,小說家和文學作品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,而另一方面,電影導演又常抱怨好的劇本好的故事太少。對此您怎么看?
鮑十:大多數優秀的電影,人物形象豐滿、思想內容深刻,都是從文學作品改編過來的。這已經是一個共識。小說家在創作的時候,調動了自己豐富的生活積累,嘔心瀝血,才能寫出一部好的小說。當這樣的小說要改編成電影,它的內涵、細節自然比其他劇本好很多。而不是改編自優秀小說的電影劇本,大多出自職業編劇。他們寫的劇本,往往會存在一個問題——編造的痕跡比較重,讓觀眾覺得假。
上世紀80年代,這個現象就非常明顯。
職業編劇可能過于注重情節了,這是他們的一個突出問題。編劇和作家寫小說其實是不同的兩種寫作方式。而現在的電影,實際上是有套路的,形成了套路。但好的小說卻不能陷入任何套路之中,也不能跟任何作品重復。
羊城晚報:現在年輕的寫作者,很多都想做編劇,您是怎么想的?
鮑十:以我有限的經驗來看,我不建議一出來就寫電影、電視劇,這樣的成功率比較低。電影的產出量實際上非常有限,周期也比較長,知名的導演就那么幾個。一開始就投身寫劇本,我覺得比較冒險,從最實際的角度出發,我建議還是先寫小說,小說發表的可能性比較大,全國這么多刊物,還有幾乎沒有門檻的網絡平臺,發表小說是相對容易的。而寫電影就不一樣了。倒不如先寫好小說,好的小說出來了,就可能有導演來找你。












 金正恩向中朝友誼塔送花圈
金正恩向中朝友誼塔送花圈 投下超8.5萬噸炸藥 以軍已完全摧毀加沙126所學校
投下超8.5萬噸炸藥 以軍已完全摧毀加沙126所學校 36年巡邊護邊 他做3號界碑的守望者
36年巡邊護邊 他做3號界碑的守望者 傳承抗美援朝“空中拼刺刀”精神 新時代空軍官兵磨礪鋒刃逐夢空天
傳承抗美援朝“空中拼刺刀”精神 新時代空軍官兵磨礪鋒刃逐夢空天 財政部:1—9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63059億元
財政部:1—9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63059億元 全國汽車報廢更新補貼申請超過157萬份 補貼申請量呈現快速增長態勢
全國汽車報廢更新補貼申請超過157萬份 補貼申請量呈現快速增長態勢 60元買下“國際競賽”獲獎證書?記者調查山寨賽事亂象
60元買下“國際競賽”獲獎證書?記者調查山寨賽事亂象 警方回應“男子毆打女子致吐血”視頻:為吸粉擺拍 已拘留
警方回應“男子毆打女子致吐血”視頻:為吸粉擺拍 已拘留






| 那曲县 | 雷波县 | 许昌市 | 灵山县 | 千阳县 | 镇坪县 |
| 灌南县 | 兴城市 | 错那县 | 义马市 | 北宁市 | 错那县 |
| 岫岩 | 广元市 | 漳浦县 | 阜城县 | 玉山县 | 永善县 |